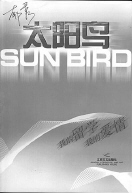

继《花季·雨季》之后,郁秀推出了反映留学生活的长篇《太阳鸟——我的留学我的爱情》,在这部轻松、幽默、充满青春气息的长篇小说里,我们读到了一种校园文学风格的延续。
杨一的名字简单。别人常跟她开玩笑:如果你有弟弟妹妹是不是跟着叫杨二杨三啊?明知这是个玩笑,却偏是一本正经地回答:也许吧。目的是让开玩笑的人笑不出来。越是年长,越是体会到这个简单名字的妙不可言。父亲是个资深记者,舞文弄墨之人,起个一笔之名,简直是大智若愚。杨一顶瞧不起有些同学的名字,是翻着《康熙字典》挑肥拣瘦得来的,什么刘躞、赵蠲,欺负我国六分之一的民众是文盲,连老师也一并考倒。第一节课,老师点名,只能叫“王什么”同学、“赵什么”同学,叫到杨一的名字,老师心存感激,终于碰上他认识的字了。同学们都羡慕杨一成绩好,杨一说,是啊,等你们把名字写完,我已经做完两道题了。
和中国这一代所有的独生子女一样,成长,就是承担家庭的期望。出生于70年代末,中国开始开放,中国人开始逐渐过上好日子的时代,杨一会这样想,是因为她母亲常叹她自己生错了年代。父亲、母亲同属老三届。他们这一代人最苦,该发育的时候,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没饭吃;该读书的时候,赶上文化大革命没书读,还要去上山下乡;该结婚的时候又没房子没工作;好不容易安稳了几年,又碰上了下岗,怎么什么倒霉事都让他们这一代人摊上了。他们常常念叨,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子女应该聆听且牢记的,只是杨一听时远没有他们希望的虔诚,时而冒出一句:“你们说到哪儿了?”
他们说倒在其次,关键是他们做了。对下一代,他们急于将他们自己不曾拥有的给杨一。杨一三岁识字,5岁上学,6岁背唐诗300首,7岁学钢琴,8岁学画。杨一小时候是属于“光长脑袋不长肉的孩子”,当然现在的丰满健康是后话了。童年的记忆就是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从这个学习班奔到那个训练班。父母最常说的话是,不要老是玩,玩玩玩,玩能玩出个名堂吗?杨一真是比窦娥还冤,她什么时候玩过了?她比上班的人还忙还累,人家还有下班、周末,她是24小时处于战备状态。
童年的杨一也有不得已,涕泪交流,抗议示威。母亲当即哭天抹泪,竟然比她还伤心地说,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,父母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为你创造条件,你不要辜负了我们,我们都是为了你。到底谁为了谁?杨一一直觉得她是为了他们。她投降了。邻居刘阿姨说,还是你们家杨一听话懂事,我送我们女儿学琴学画,她学什么都是半途而废。杨一抿抿嘴,心里在说,那是因为我实在哭不过我妈。
母亲说话频率很高,含量很低,说来说去,就是那么几句,后来母亲刚开一个头,杨一就能接下去说了。比如母亲说“我们小时候啊”,杨一拿腔拿调接着道:“苦得不得了,如果有你们现在这样的条件,一定会干番大事业的。”母亲瞪了她一眼:“你知道就好。”杨一知道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,家里经济并不很好的时候,母亲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,还向两个舅舅借了钱给她买钢琴。父母对自己很苛刻,舍不得吃舍不得穿,近似自虐。
杨一总算不负众望。不管在哪一方面,她都成了明星。她认为读书是件很简单的事,读不好书反而令她不解。“不就是一本书吗!”她说。
她的字画屡屡得奖,她的字画比她本人早十来年到达美国与美国人民见面。
她的文章深刻老到,完全不见中国女性文章中的小家子气和矫揉造作,通过她的文章,叫人既想象不出她的年龄,也猜测不到她的性别,加上她那中性的名字,于是源源不断收到女生的求爱信,开头千篇一律地称之为“亲爱的杨一老师”。
杨一在学生时代出尽了风头,她觉得自己比校长还忙。她精力充沛,既是篮球队的队员,又是舞蹈队成员,常常刚在柔和的音乐声中优雅一番,舞鞋一脱,球鞋一穿,又在球场上冲锋陷阵了。这是两码子事,怎么转得过来?
杨一就像戏文里唱的——“谁说女儿不如男,呸,那是万恶的旧社会”。然而男生因为孤独而优秀,女生因为优秀而孤独。在中学生这个最真诚又最不真诚的年纪,杨一这种风光的女生在班上并不讨好。十几岁的孩子尚未学会掩饰情感,表达起来爱憎分明。班上一个女生这样对她说:“杨一,我不喜欢你,你太出风头了。”另一个男生对她说:“杨一,你不应该和我们这些平凡人作朋友,名人应该与名人交往。”果然,男生的话刚说完,班主任就来叫:“杨一,电视台来人找你。”
有家电视台要采访北京市优秀中学生代表,杨一是代表之一。问到业余爱好时,少年才俊们面对荧屏侃侃而谈,这个时候没有人说到四大天王,都是萧邦、李斯特;没有人说王朔,都是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,尽挑高雅的。轮到杨一,她说:“我没有什么爱好。”主持人问:“那你平时喜欢做些什么?”杨一想了想,回答:“做菜。”主持人愣了一下,杨一以为人家不明白,又加了一句:“因为我爱吃。”主持人又问大家有什么愿望?杨一这次抢先回答:“我想吃遍天下美食。”后面几个同学,这个说环游世界,那个说世界和平,杨一眨眨眼睛问主持人:“要说这些吗?”主持人笑笑:“随便,自然就好。”杨一乐了,又说:“我想吃遍各色的小餐馆……”主持人不得不打断她:“时间有限,你就说到这儿吧。”节目播放出来时,杨一这段被砍掉了。
自古才女多傲气。杨一正常,正常得接近平庸。既不前卫也不新潮,既不清高也不孤傲,既不深沉也不古怪。她能说会道、爱开玩笑,有时还会冒出一两句粗话,“好个屁”、“去他妈的”,语惊四座。让人汗颜。之后她再甩出一句最常说的:“逗你玩的。”
有一次,杨一数学竞赛得奖归来,一家报社的记者要采访她,打电话与父母约好星期六早上八点半。星期六早上,母亲八点钟叫醒她说:“别睡了,客人马上就到了。”杨一揉着惺松的双眼,道:“有没有搞错,这么早就要我接客。”双亲大眼瞪小眼。母亲连忙说:“孩子,这话待会儿可不能乱讲。人家不是以为你有病,就以为你父母有病。”杨一像是醒了,咧着嘴傻笑,又是那句话:“逗你们玩的。我要是连这个分寸都没有,怎么混到今天!”
又有一次,杨一对母亲感叹:真正聪明的女人是比自己的丈夫笨那么一点点的女人。女人太聪明太能干,着实让人害怕,尤其是男人。杨一与母亲分享此心得,母亲感慨不已。不是因为这句话,而是说这句话的女儿年仅16岁。现在的孩子太早熟了,他们十六岁时什么都不懂,现在16岁的孩子没有什么不懂的。母亲和父亲商议了一番,觉得很有必要与女儿谈一次。
饭桌上,父母双亲神情紧张而严肃。母亲对父亲使了个眼色,示意父亲开口;父亲又对母亲点了点头,要母亲开口。杨一像是浑然不觉,只管吃她的饭,喝她的汤,还故意啧啧地咂着嘴。吃饱了喝足了,说句“好吃”,又抹了一下嘴,说道:“你们要对我说什么,就说吧。”母亲皱皱眉头,支吾了一阵,说:“是这样的,你虽然只有16岁,但马上就要进入大学了,在你们这个年纪,会觉得有些事情很神秘,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。”
“妈,你在说什么啊?”
“比如说,比如说性。”母亲显然有些不好意思。
杨一站起来,边回房间边说:“哦,我早就不觉得神秘了。”
父母二人盯着杨一的背影,又相互对望,父亲对母亲说:“明华啊,我听你女儿这话,怎么这么害怕呀。”
传来杨一咯咯咯的窃笑声。
父亲说:“你笑什么?”
杨一转身,扔来一句:“我逗你们玩的。”
她就是这么一个活灵活现的女孩儿。
有一个同学对她说:“你怎么样看怎么样像胡同里长大的。”杨一至今仍觉得这是对她的赞美。杨一讨厌做作。
